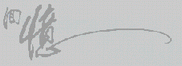
~~ 路 上 的 傳 說 ~~ .黑 痣.
作者:不詳
林晏如走了,從被診斷得乳癌到離開人世,她只度過八年的美麗人生;我的病人也走了,可是,她只活了一年。
當我看著陳先生忍住淚水,緩緩的替小惠套上結婚戒指,不聽話的眼淚,還是從我的眼中奪眶而出。
小惠今年才二十六歲,是一名國中老師。一年前的盛夏,她來到我的門診。第一次見到她,我就被她特殊的氣質所深深吸引。
她總是面帶笑容,笑得比夏日午後的陽光還要燦爛。
她脫下右腳的鞋子問我說:「陳醫師,我腳底長了一個黑色的痣,不曉得有沒有關係?」
我仔細的看著她所指的地方,有一個直徑大概八厘米大小的黑色丘疹,邊緣雖然還算規則,可是顏色卻有點斑駁。
「這長多久了?」
「有好一陣子了,我想說應該沒什麼關係;而且長在腳底,覺得給醫生看不太禮貌,我就一直沒管它。是最近和學生一起打球時扭到腳,校醫幫我纏繃帶時發現的。她堅持要我一定要來檢查一下。」
「這個最好切掉送病理檢查比較好。」
小惠聽到我說要切除,顯得有些遲疑。經過我一番解釋之後,她才點頭答應。
這是一個門診小手術。在局部打一針麻醉劑之後,大約十五分鐘就完成了切除和縫合。
我和小惠相約兩個星期後看報告。為了避免她無謂的擔憂我對可能發生的事情,並沒有講得很清楚,接下來的兩星期,我獨自默默的替小惠祈禱,希望病理報告只是一個黑痣。
很快的兩週過去了,小惠又帶著她標準的笑容出現在我的診間。面對她的笑容,我前一天晚上一夜未眠反覆思量所準備的說辭,卻始終說不出口。當然,最後我還是對他說出了皮膚科醫師最不願對病人宣告的六個字『黑色素細胞癌』,並且仔細的解釋它背後所代表的涵義以及一些即將到來的挑戰。
小惠聽完這些話,反應還算冷靜;她只是靜靜的聽著。接著和她討論住院要做的全身電腦斷層及骨骼掃描時,她也只是點點頭,一言不語。
當我說完停下來,小惠和我就這樣無言相對的坐著。凝重的氣氛,彷彿凍結了診所間的時空;隨後的蟬鳴聲,打破了寧靜,也讓這忙亂的人世,繼續滴答滴答的走下去。
那天是我最後一次見她的笑容。接下來,一連串的黑色追緝,就在你我都希望有美好結局下展開。
經過精密的檢查,腫瘤並沒有任何轉移的跡象。根據這個令人略感欣慰的結果,小惠又進了一次開刀房;我們將原來已經切除腫瘤的部分,做一個更大的切除。這樣做是為了確保不放過任何可能已經游離出來的壞細胞。整個過程,相當順利;在論及婚嫁的男友陳先生的悉心照料下,她顯得相當堅強。
接下來的六個月,小惠固定回門診追蹤;每一次她總會帶來一些自己在醫學期刊上所到的資料和我討論。六個月過去,她幾乎成了黑色素細胞癌的專家了。
只是,當她懂得越多時,她越不肯答應陳先生的求婚。
就在過年前夕,小惠忽然面帶不安的出現在我面前,比預定回診的日子,早了半個月。
「陳醫師,我在右邊鼠蹊摸到了一顆淋巴結。」我馬上為小惠安排檢查。結果,斷層掃描顯示,除了摸到的這一顆,深部還有兩顆淋巴結。
就這樣,小惠在大家逢人就說恭喜的大過年裡,住進了醫院。過年期間,醫院總是一片死寂,每天只有從十五樓的憂暗角落,傳來陣陣的啜泣聲。小惠終日以淚洗面;因為,當我們進入開刀房將鼠蹊劃開時,一粒粒黑色的淋巴結,嘶牙裂嘴地對著我們笑著,恥笑著醫學的無能。
十天過去,小惠和陳先生和我告別。經過討論,她們決定放棄化學治療,尋求中醫的協助。我沒有多說什麼,因為我知道化療對黑色素細胞癌的反應不好。
我只有獻上最深的祝福。當了醫師這麼久,我體會到一件事,只是祝福,有時候真的沒什麼用。
就在一個月前,也就是他們離開的半年後,小惠被送到了急診。轉移到肺部的癌細胞,已經讓她喘不過氣來;看著她挺著裝滿腹水的肚子,水腫到有點變形的雙腿,我只能和陳先生默默相視。轉上來病房沒多久,小惠終於陷入昏迷,她始終沒答應陳先生的求婚。但是,一向順著小惠的陳先生,還是在隔天的清早,從口袋中拿出了準備了好久的戒指,緩緩的幫小惠戴上。
黑色素細胞癌,這個每年造成六千八百個美國人死亡的可怕疾病,所幸在中國人並沒有如此常見。但是,不幸的是,中國人最常得到的黑色素細胞癌,卻是黑色素細胞癌中最容易死亡的一型:肢端型黑色素細胞癌。
這個可能長在手掌、腳掌或是指甲下面的黑色怪獸,正是奪走小惠生命的兇手。
後 記
生命是否因脆弱而寶貴?我不知要如何回答,只是只能叮嚀
請注意:如果你身上有黑痣∼∼
Oldldy 2003 冬夜
黑痣-
因為它是從我們人體皮膚的黑色素細胞產生惡性變化而來,所以可以發生在全身任何一塊皮膚;它可以突然出現,也可以由原本看起來像是黑痣的東西轉變而來。因為早期發現就將它切除,是避免日後奪走我們寶貴生命的唯一方法,我們每個人應該要每個月定的檢查一下自己身上的黑痣,並記錄下來;一但有下面的情況,就應該求助皮膚專科醫師,做進一步檢查。
A.
Asymmetry﹝不對稱﹞:你的黑痣左半邊和右半邊看起來不一樣。
B.
Border﹝邊緣﹞:黑痣的邊緣有突出、凹陷等不規則的情況。
C.
Color﹝顏色﹞:整個黑痣的顏色不一致,例如有黑色、棕色和咖啡色交錯。
D.
Diameter﹝大小﹞ :黑痣的直徑變大。
此外如果任何一個黑痣有發癢、流血、或潰瘍的情形,也應立即接受檢 查;而手掌、腳掌即指甲附近的黑痣,請直接找皮膚專科醫師檢查。
每個月花個十五分鐘,複習一下上面的ABCD,就可以救你自己一命。別讓你成為下一個小惠!